
北巷、王小立、Buddy、枯叶工房、CMJ等作者的漫画作品。(冯庆超 制图)
川贝的漫画之路始于传统纸媒时代。他曾在漫友旗下杂志《漫画SHOW》担任编辑。2013年,这本承载着许多人青春记忆的杂志因发行量不足宣告停刊,成为行业洗牌的一个缩影,不少同事就此黯然离场。
川贝记挂着“还有一些作者需要照顾”,转投同集团的《漫画世界》。然而,仅仅一年左右,他便感到与新的工作环境在核心理念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差异,最终选择了离开。
他的离开仿佛一个预兆。2016年,《漫画世界》也悄然落幕。至此,国内原创漫画杂志的黄金时代逐渐远去,格局重构,形成了业内常说的“御三家”,即发行量巨头《知音漫客》以及紧随其后的《飒漫画》《神漫》。
最终,川贝从纸媒编辑转行为一位自由职业者,依然服务于漫画创作者和工作室。他不隶属于任何公司,由漫画家们私人雇佣,帮他们打理作品的商业运营事务,如版权洽谈、市场推广、合作对接等。
私人经纪人的角色之外,川贝也为漫画工作室担任顾问。他观察到,国内大部分工作室的核心模式是承接来自大公司或平台的外包订单,专注于按需生产,鲜少涉足拥有自主版权的作品创作和运营。在这种“外包驱动”的模式下,川贝的角色是在工作室承接项目时对创作方向和品质进行专业把控;同时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和读者,进行品牌建设、宣传推广等深度运营,引导工作室从“代工”跨越为“品牌”。
这些年,川贝亲身经漫画载体的荣枯变迁,目睹漫画行业的起落沉浮。以下是他的观察。
进入网络时代后,宣传的权重变得大了很多,哪怕只是平台编辑,也必须一个人做一整个宣发团队的事情。作为经纪人的话,要想的就更多了,涉及漫画家日后的路线问题。
提升作品质量需要专业知识,判断情节、画面、分镜如何吸引人,如何触动读者内心。但在互联网免费阅读时代,标准几乎是一面倒地倾斜在阅读数据上。通过质量提升数据增长,通常远低于通过数量更新带来的增长:多更新一次带来100%增长,画得好可能只提升30%-40%。因此,在平台主要策略下,专业性需求丧失,责编只需催来更多稿子。剩下的过审与否,几乎全凭主编拍脑袋,甚至导致腐败现象——某些编辑关联的工作室通过连载企划后,工作室以回扣形式返还部分稿费。
更核心的是,编辑在公司体系内变得不重要,重要性让位于融资、商务等部门。编辑能操控的资源(如宣传位)话语权也持续下降直至消失。上层更关注将流量粗暴兑换成广告收入。
实际工作中,作者与互联网平台编辑交流创作、宣传、艺术等意义很小。因为对接编辑层级低、职权小且高度不专业,他们既无能力也无资源推动任何事情。作者最终感觉编辑只是“收稿的”,其他讨论都难以实施。很多编辑基本上1到2年内就会改行离职,相关技能没有办法传承下来,传承下来也没用,没有职权、没有资源。
更悲哀的是,不仅是责编成本,漫画作为商业项目的运营成本几乎全部转嫁给了责编和漫画作者。在纸媒时代,这个现象已经有一点端倪,发行部无限接近于物流部门,将宣传等都转嫁给编辑身上。发行渠道本身不专业这一系列问题被当时较好的大环境掩盖住,互联网时代平台缺钱后,这个矛盾凸显至非常严重的状态。

《漫画SHOW》。(资料图)
这一模式后来被证明完全错误,但奠定了现在漫画行业的先天不足。当时行业憧憬互联网能打破传统发行的桎梏,但互联网资本消灭了漫画的心理价格和社会价值认同。为了获取用户,所有漫画免费阅读。这件事情持续了很长时间,导致社会大众认为漫画不需要花钱看。
互联网资本用比纸媒更低的稿费约稿,让漫画家通过加大产量提升收入。阅读量短时间内膨胀到过亿规模,但作品本身“传单化”,成了免费宣传品。大家是不会为可以随手拿到的传单付钱的。在日本漫画行业最兴盛的时候,付费依然占据了整体营业额的3/4,但国内把这3/4的营业额全部抛弃了。
2017、2018年后,互联网平台估值泡沫破裂,不得不寻找新盈利模式。但他们没有鼓励原创或开发周边,而是全面转向网络小说化,直接照搬起点中文网等网站的定价、运营方式和作品定位。腾讯漫画等平台更将漫画兼并成为网络小说的下游产业,强力推动小说改编漫画。大量原创项目被腰斩,作者要么画改编作品,要么离开平台。实际运营中,绝大部分改编作品活不过两年甚至一年就被腰斩。
日后稿费缓慢增长,中游作者可能从100多突破200元(每页),逐渐逼近250元。后续整体外包形式出现,作者接触来自动画、游戏公司或其他的大型商业项目,当时行规默认,因为作者不享有著作权相关衍生收益,需支付更高稿费补偿版权损失,这让稿费额又往上涨了一些。大概到2016年左右,《知音漫客》支付给普通二线作者的稿费相比2009年高至少三成以上。2014到2016年,稿费大概维持在350到400元左右。
互联网企业入场后,参照纸媒标准,但往下降了一些,鼓励作者通过画更多稿量获取收入。网络平台与杂志的最大区别,是杂志受成本限制,版面量有限;互联网平台资金充裕,且不存在版面概念。互联网当时给予行业内的憧憬是更自由的表达,且无版面限制,让更多作者有机会入行获得连载成为职业人。除超一线作者,一般作者已出现明显通过刷量获取更高总收入的现象。他们以较低门槛获得连载,稿费低但可刷量,月收入比杂志连载上限多得多。
这形成两个作用。第一,刷量逐渐成为行业主流想法。第二,互联网平台作为企划发起方或著作权所有方,以外包形式发给漫画作者的作品增多。互联网稿费可能低于杂志,但作为外包作品,因无著作权,可获得更高稿费作为补偿。这样哪怕稿费只有纸媒时代六到七成,但允许刷产能,单位时间可获得两到三倍于纸媒时代的稿费。以此为基础,工作室逐渐转向流水线、以加大产能为目标的运作路线。
最膨胀的2015、2016年后,泡沫破裂,互联网平台开始宣称行业寒冬。一两年内,几乎所有平台都拖延了稿费,一些二线平台倒闭。风波后稿费额开始掉头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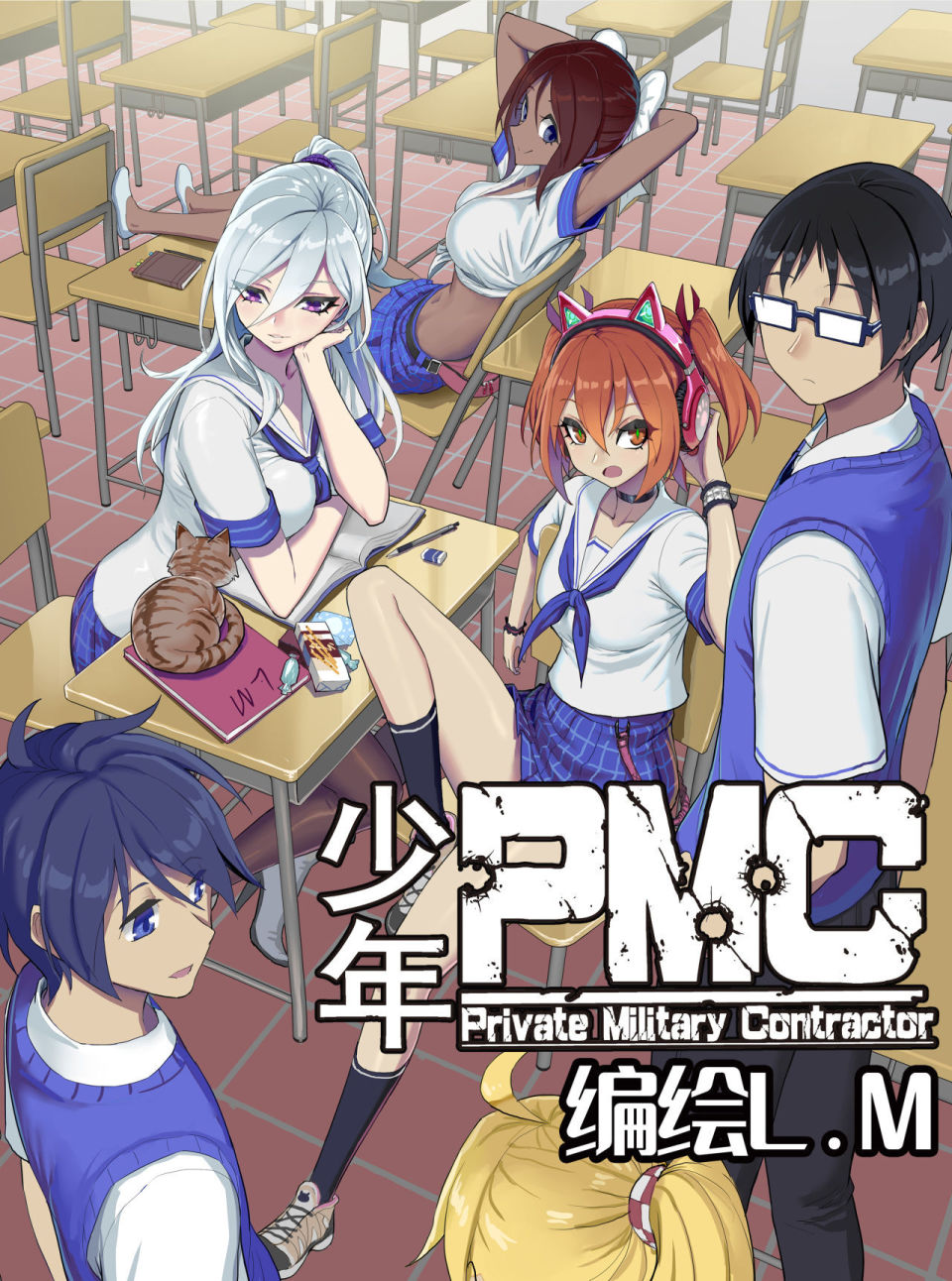
川贝合作漫画作者L.M的作品。(受访者供图)
那几年(各大平台)都走这条路。但很多拿来改编的小说商业价值并没有表面的数据写得这么好,改编结果不好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很多小说不适合改编漫画,原作的读者也不认同。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些小说本身价值不足,反而漫画作者被用来通过改漫画的形式来证明原作价值。
平台又有另外一条路线,编辑完全指定模板,作者或工作室必须完全照着模板创作。虽然看上去是原创,实际上和改编小说很像。这两种模式导致作者只能获取越来越低的单页稿费,创作量大但原创性低,著作权也完全失去了。
纸媒由于国内批发经销渠道高度不专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路径依赖效应,《斗罗大陆》卖得好,那么就只想卖类似《斗罗大陆》漫画版的东西,不想做任何其他的尝试。这种小农式盲目跟风的经营理念,带来了盲目投入网络小说漫改的热潮。
而这种盲目性在互联网行业造就的IP金融热潮中,变得更加普遍。在漫画行业进入网络时代后,有两个驱动力在背后支撑着网络小说漫改的产能需求:一个是大网络平台基于流量数据估值融资的盈利模式,本身需要极其大量的作品去填充纸面数据;一个是网络小说平台背后的资本,需要通过改编漫画项目来作为自己手中小说版权的估值数据支撑。
席卷本质是建立在互联网巨头试图通过金融估值,而非实际销售来获取利润而强行造就出来的虚假繁荣。这个虚假繁荣在融资泡沫破裂后仍然因为巨大的惯性,以及大量原有专业人员离开行业,留下的专业性较低的人不懂如何正常使一部漫画作品盈利,也失去原有的产业链支持,而成为目前的主要形式。被破坏的正常产业体系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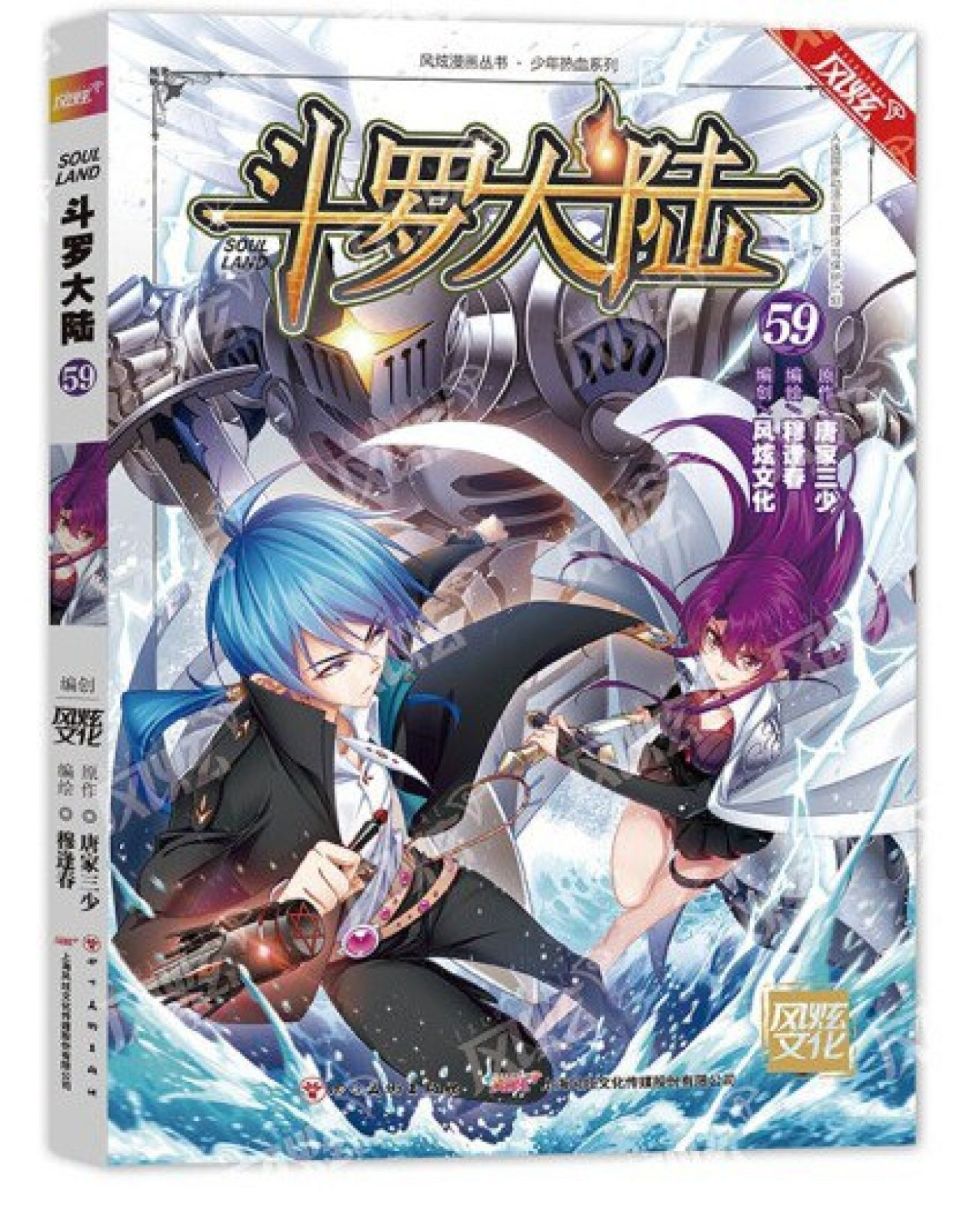
《斗罗大陆》漫画版的成功开启了网络小说改编漫画的潮流。(资料图)
第二则是以大连糖人家为代表,漫画家是淳良猴子和鱼正义,他们也接受腾讯的投资,不过主要行动方向是以各种方式去培育自己的IP,在公司内制作动画、发展周边产品、参加漫展摆摊宣传等等,而不仅是提供漫画内容产出,相对独立性和积极性更高。
第三类和第一类相似,都是被平台背后的资方以投资形式买断的内容供应方,但他们基本上只考虑制作本身,获得收入的方式也几乎仅限于平台发放的稿费和少量额外分成,更像是一批独家签约作者,只是以投资形式进行。
几乎所有的被投资的作者或工作室团体都会面对营收单一的问题。营收单一的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当前整个大行业的问题——产业体系的严重欠缺和被破坏,由于这种脆弱性,即便资本有热钱快速投入收购,也无法长期稳定地支撑起创作产出。
但是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之后,(平台)基本上打底就是全授权,而且没有任何约束,例如关于版权收益的回报是没有的,合约金是没有的,时长从以前大概5年,变成了自作品完结起计算的5年甚至10年,后面增加到15年、20年,相当于几乎不可能通过自然时间等待合约结束。所以基本可以视作,作者完全失去了著作权,而且也没有作者能够成功从平台重新获取自己签给平台,但没有得到任何使用的著作运营权。如果你要尝试去回购,平台会要求你把此前支付的所有稿费全部交还,才有可能商谈著作权交还。这个条件其实挺荒谬的,因为(作品)运营了这么久,没有运营出收益,而且签订时基本的网络传播权也售出应用了这么久。平台处于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的状态,但是作者要承担巨量风险成本。
我的工作就是重新补充平台本应承担的部分。我需要接触到宣传和产品运营,包括策划宣传活动,寻求交换宣传资源的合作,还有社交网络账号的维护。现在我们甚至不得不开始把若干作品上传到盗版网站上宣传。
特殊环境形成这样啼笑皆非的结果。在一个没人管的盗版网站上,反而可以获得更好的投放量,现在很多作者有不被故意限流的曝光量,就已经很高兴了。
目前对于作品的宣传,甚至开始走向更原始的、像纸媒时代的状态,读者口耳相传,通过作品属性尝试进入兴趣圈子。从广域流量里,把有效读者过滤出来,转入私域环境,减少互联网限流带来的信息丢失。
我们也尝试过在一些互联网平台发布内容,如果是漫画家单独投放付费章节,会遇到问题。一个是平台分成要求过高,但是并不提供正常的宣发曝光率且平台自身流量资源也非常劣质(指付费转化比例极低);第二个是定价权,平台会控制定价,不允许单章节提价或做高浓度章节,甚至要求必须是全彩条漫,所以这条路没给原创作者太多帮助。
举个例子,日本电子漫画的总营业销量和营业额也在近两年超过了它的常规出版营收,但日本的电子漫画平台,主要由传统出版社主持创办、基于杂志作品电子化,它的定价销售及作品技术指标与纸媒杂志区别不大,唯一特殊的是降低点价格,比如电子版单行本售价大概是纸媒的七八成。所以网络大潮并未对他们造成很大影响。
日本漫画编辑林士平曾表示,无法理解中国完全免费或极低价格的漫画形式,因为这样肯定入不敷出。他点明了互联网漫画入场阶段奠定的形式,构成了行业基因上的绝对缺陷,导致目前漫画最大的问题是,若无外界供给,很难完成自我造血和经济循环。资本主导的主流漫画行业,自身赚钱能力是被质疑的,这与已证明可行的纸媒时代形成最大区别。
现在,只有很少作者能在互联网体系下保持存活。在我看来,作者自身经济价值被挫伤,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作者选择跳出来,所有东西都自己干,试图回到定价更适中的、有若干周边产品体系的、更传统的形式,这样反而带来更合理收益。但这样做需要勇气,且失去了杂志基础稿费支持,意味着在作品实现收益、维持生活之前,作者需依靠存款或做其他工作支撑。
在纸媒时代,新作者连载前三年,产品收益很低,不足以维持稿费。当时的成本平衡,本质是通过已有名气的老作者带领、帮扶新作者,通过杂志将所有作品强行打包进一个商品,让读者付费。这补贴了新作者,扶持他们走向成熟,并让年轻漫画家的作品获得应有曝光量。而现在我们不得不付出数倍努力,承担更大风险,才能重新获得这一经济循环。
近年有两个舆论事件。一是有位漫画家在微博上提问,为何商业化同人创作做得很好的人不去做原创?引发大量同人创作者指责网暴,说他居然敢认为原创高于改编、高于二次创作。若在日本,原创与改编确实有等级差距,现在国内原创反而成了边缘。
二是关于“国漫”词语的争议。“国漫”在大多数人意识中代表动画,这恰好始于2013到2014年互联网入场漫画和动画时。当时漫画因纸媒多年经营有号召力,互联网资本通过舆论操作,结合“动漫”概念,将“漫”字挪用至动画宣传。动画在资本体系中占据更高地位,能花更多钱,估更大值。挪用未被察觉反思,十多年后漫画作者提出“国漫”应指国产漫画,又激起网暴。
漫画的社会认同,近一两年才由坚持原创、坚持质量为第一指标的作者重新慢慢拾取,从头再来。


